老字号味道唤醒城市记忆,“光明好市”沉浸式市集开进金茂大厦
老字号味道唤醒城市记忆,“光明好市”沉浸式市集开进金茂大厦
老字号味道唤醒城市记忆,“光明好市”沉浸式市集开进金茂大厦 无斑雨蛙栖息在枯叶上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在上海奉贤区头桥街道的北宋(běisòng)村,拇指大小的蛙趴在叶子(yèzi)上晒太阳,通体青绿,半眯着眼,只有下巴(xiàbā)呼吸鼓动,三五成群,人靠近也没能惊扰——这是无斑雨蛙。
70公里外(wài)的青浦区张马村,和泥土(nítǔ)几乎融为一色的“大个头”蛙,从水岸边的洞口探出半个身子(shēnzi),背部布满凸起的纹路,一旦觉察异样便迅速逃离,一跃有一米多远——这是虎纹蛙。
夏夜的池塘边、农田旁,蛙鸣依稀可闻,然而少有人(yǒurén)注意到(dào)蛙声与蛙声的区别。过去几十年间,有些蛙鸣的声音渐渐小了,直至在野外彻底消失,无斑雨蛙(yǔwā)、虎纹蛙这样的上海原住民就在其中。
根据2013年至(zhì)2015年开展(kāizhǎn)的上海市第二次陆生野生(yěshēng)动物资源调查,上海可见的野生蛙类仅有中华(zhōnghuá)蟾蜍、金线侧褶蛙、黑斑侧褶蛙、泽陆蛙、饰纹姬蛙、北方狭口蛙这6种。无斑雨蛙和虎纹蛙近一二十年内没有被发现。
物种的(de)消失,意味着生态链的一环缺失,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的平衡被打破。为了让本土蛙“重返家园”,一群人正在努力,在北宋村建立雨蛙生态农场,在张马村(zhāngmǎcūn)打造虎纹蛙(hǔwénwā)等野生动物栖息地,为它们重新营造适宜的生境。
无斑雨蛙栖息在枯叶上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在上海奉贤区头桥街道的北宋(běisòng)村,拇指大小的蛙趴在叶子(yèzi)上晒太阳,通体青绿,半眯着眼,只有下巴(xiàbā)呼吸鼓动,三五成群,人靠近也没能惊扰——这是无斑雨蛙。
70公里外(wài)的青浦区张马村,和泥土(nítǔ)几乎融为一色的“大个头”蛙,从水岸边的洞口探出半个身子(shēnzi),背部布满凸起的纹路,一旦觉察异样便迅速逃离,一跃有一米多远——这是虎纹蛙。
夏夜的池塘边、农田旁,蛙鸣依稀可闻,然而少有人(yǒurén)注意到(dào)蛙声与蛙声的区别。过去几十年间,有些蛙鸣的声音渐渐小了,直至在野外彻底消失,无斑雨蛙(yǔwā)、虎纹蛙这样的上海原住民就在其中。
根据2013年至(zhì)2015年开展(kāizhǎn)的上海市第二次陆生野生(yěshēng)动物资源调查,上海可见的野生蛙类仅有中华(zhōnghuá)蟾蜍、金线侧褶蛙、黑斑侧褶蛙、泽陆蛙、饰纹姬蛙、北方狭口蛙这6种。无斑雨蛙和虎纹蛙近一二十年内没有被发现。
物种的(de)消失,意味着生态链的一环缺失,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的平衡被打破。为了让本土蛙“重返家园”,一群人正在努力,在北宋村建立雨蛙生态农场,在张马村(zhāngmǎcūn)打造虎纹蛙(hǔwénwā)等野生动物栖息地,为它们重新营造适宜的生境。
 5月28日,一批无斑雨蛙被放入大型网箱(wǎngxiāng)实验(shíyàn)样地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无斑雨蛙的“高颜值”是公认的。成年个体体长大约(dàyuē)在3-4厘米,拇指般娇小,背部通常呈现出清新的绿色(lǜsè),腹部洁白无瑕,体侧和大腿没有任何斑点,纯净可爱(kěài)。
5月28日,一批无斑雨蛙被放入大型网箱(wǎngxiāng)实验(shíyàn)样地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无斑雨蛙的“高颜值”是公认的。成年个体体长大约(dàyuē)在3-4厘米,拇指般娇小,背部通常呈现出清新的绿色(lǜsè),腹部洁白无瑕,体侧和大腿没有任何斑点,纯净可爱(kěài)。
 无斑雨蛙(yǔwā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不同于大多数蛙类的昼伏夜出,无斑雨蛙喜欢晒太阳,经常(jīngcháng)成群(chéngqún)在高秆农作物上“聚会”,晨昏时间沐浴阳光最为舒适,光线(guāngxiàn)过强时则躲在叶片下“乘凉”。
它们(tāmen)也热衷探索不同的土地和植被类型,在水稻田(shuǐdàotián)里繁殖,长大后在玉米、棉花等高秆作物间觅食(mìshí),也可在果园、树林中栖居。冬季则躲进落叶堆或土壤中冬眠,翻耕的菜地、稻田容易让它们丧命。
无斑雨蛙的发现(fāxiàn)要追溯到1888年,德国动物学家奥斯卡·博特格在上海首次发现并命名(mìngmíng)它,这(zhè)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在上海被发现和命名的蛙类。
据老一辈的野保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回忆,过去每到水稻育秧期,这种绿色(lǜsè)小蛙就集中在稻田(dàotián)里繁殖,数量十分庞大,农民将它们捕捉后一盆盆地喂给鸭子吃。
然而,近二三十年,随着城市化进程(jìnchéng)加速、栖息地(qīxīdì)丧失以及农药滥用,无斑雨蛙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。上一次在(zài)上海发现它们自然活动的踪迹,还是十几、二十年前在南汇、奉贤和浦东交界处的农田果园。
无斑雨蛙(yǔwā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不同于大多数蛙类的昼伏夜出,无斑雨蛙喜欢晒太阳,经常(jīngcháng)成群(chéngqún)在高秆农作物上“聚会”,晨昏时间沐浴阳光最为舒适,光线(guāngxiàn)过强时则躲在叶片下“乘凉”。
它们(tāmen)也热衷探索不同的土地和植被类型,在水稻田(shuǐdàotián)里繁殖,长大后在玉米、棉花等高秆作物间觅食(mìshí),也可在果园、树林中栖居。冬季则躲进落叶堆或土壤中冬眠,翻耕的菜地、稻田容易让它们丧命。
无斑雨蛙的发现(fāxiàn)要追溯到1888年,德国动物学家奥斯卡·博特格在上海首次发现并命名(mìngmíng)它,这(zhè)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在上海被发现和命名的蛙类。
据老一辈的野保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回忆,过去每到水稻育秧期,这种绿色(lǜsè)小蛙就集中在稻田(dàotián)里繁殖,数量十分庞大,农民将它们捕捉后一盆盆地喂给鸭子吃。
然而,近二三十年,随着城市化进程(jìnchéng)加速、栖息地(qīxīdì)丧失以及农药滥用,无斑雨蛙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。上一次在(zài)上海发现它们自然活动的踪迹,还是十几、二十年前在南汇、奉贤和浦东交界处的农田果园。
 无斑雨蛙栖息在水稻田边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根据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包·阿迈尔(Borzée Amaël)的(de)研究,无斑雨蛙在整个华东地区的数量(shùliàng)(shùliàng)都显著减少。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,IUCN(国际自然保护联盟)对它的评级是(shì)“无危”,而事实上,它的野外种群数量可能(kěnéng)早已骤降到几百只左右的极度濒危级别。
目前,无斑(wúbān)雨蛙尚未进入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(zhòngdiǎnbǎohù)野生动物名录,但已被列入《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。
人工呵护下,重返上海(shànghǎi)
2023年,包·阿迈尔在(zài)安徽发现了无斑雨蛙(yǔwā)野生种群,采集蛙卵,孵化蝌蚪(kēdǒu),并将部分(bùfèn)蝌蚪交由城市荒野工作室饲养。经过2年多的人工饲养,200多只无斑雨蛙顺利长大,蝌蚪上岸、蛙类越冬等关键环节也已突破。
“饲养(sìyǎng)无斑雨蛙的最大难点在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资料,此前也没有人工饲养繁育的记录(jìlù),需要从头摸索。”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表示,从阿迈尔教授(jiàoshòu)手中接过蝌蚪后,给蝌蚪喂什么食物、幼蛙上岸后的成活率等难题都需要一一攻克。由于幼蛙只能捕食较小的昆虫,团队(tuánduì)专门(zhuānmén)孵化小蝗虫、小蟋蟀和果蝇(guǒyíng)喂食,“一不小心,我们办公室飞得全是蝇。”
无斑雨蛙栖息在水稻田边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根据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包·阿迈尔(Borzée Amaël)的(de)研究,无斑雨蛙在整个华东地区的数量(shùliàng)(shùliàng)都显著减少。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,IUCN(国际自然保护联盟)对它的评级是(shì)“无危”,而事实上,它的野外种群数量可能(kěnéng)早已骤降到几百只左右的极度濒危级别。
目前,无斑(wúbān)雨蛙尚未进入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(zhòngdiǎnbǎohù)野生动物名录,但已被列入《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。
人工呵护下,重返上海(shànghǎi)
2023年,包·阿迈尔在(zài)安徽发现了无斑雨蛙(yǔwā)野生种群,采集蛙卵,孵化蝌蚪(kēdǒu),并将部分(bùfèn)蝌蚪交由城市荒野工作室饲养。经过2年多的人工饲养,200多只无斑雨蛙顺利长大,蝌蚪上岸、蛙类越冬等关键环节也已突破。
“饲养(sìyǎng)无斑雨蛙的最大难点在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资料,此前也没有人工饲养繁育的记录(jìlù),需要从头摸索。”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表示,从阿迈尔教授(jiàoshòu)手中接过蝌蚪后,给蝌蚪喂什么食物、幼蛙上岸后的成活率等难题都需要一一攻克。由于幼蛙只能捕食较小的昆虫,团队(tuánduì)专门(zhuānmén)孵化小蝗虫、小蟋蟀和果蝇(guǒyíng)喂食,“一不小心,我们办公室飞得全是蝇。”
 室内养殖的无斑雨蛙蝌蚪。城市荒野工作室 图(tú)
与此同时(yǔcǐtóngshí),团队花费2年时间、走访几十个村子,最终在奉贤头桥街道找到一片(yīpiàn)拥有水稻田、菜地和植树空间的100亩复合型生态(shēngtài)农场。
“过去小农户多,家里种几亩水稻田,种点菜自己吃,种点竹林做家具,一户家庭的(de)田地就(jiù)能满足无斑雨蛙的全部生存所需。现在土地集约化管理,水稻田几百亩(jǐbǎimǔ)甚至上(shàng)千亩交由合作社经营,作物单一,再加上农药使用,无斑雨蛙没法完成生活史(shēnghuóshǐ),很难存活。”郭陶然解释,这也是它们在上海消失的重要原因。
蛙鸣(wāmíng)响起,进入繁殖期
湿热的夏天(xiàtiān)来了,蛙类进入求偶繁殖的高峰期。
5月底,24只两岁左右、雌雄搭配的无斑雨蛙蹦跳着闯入新家园——一个近300平方米的大型网箱实验样地,内设9个长方形水塘。部分塘内种植(zhòngzhí)水稻秧苗,部分栽有灯芯草、菖蒲等(děng)乡土植物,还有的什么也没种,对照(duìzhào)研究无斑雨蛙繁殖阶段(jiēduàn)对生境的偏好。
室内养殖的无斑雨蛙蝌蚪。城市荒野工作室 图(tú)
与此同时(yǔcǐtóngshí),团队花费2年时间、走访几十个村子,最终在奉贤头桥街道找到一片(yīpiàn)拥有水稻田、菜地和植树空间的100亩复合型生态(shēngtài)农场。
“过去小农户多,家里种几亩水稻田,种点菜自己吃,种点竹林做家具,一户家庭的(de)田地就(jiù)能满足无斑雨蛙的全部生存所需。现在土地集约化管理,水稻田几百亩(jǐbǎimǔ)甚至上(shàng)千亩交由合作社经营,作物单一,再加上农药使用,无斑雨蛙没法完成生活史(shēnghuóshǐ),很难存活。”郭陶然解释,这也是它们在上海消失的重要原因。
蛙鸣(wāmíng)响起,进入繁殖期
湿热的夏天(xiàtiān)来了,蛙类进入求偶繁殖的高峰期。
5月底,24只两岁左右、雌雄搭配的无斑雨蛙蹦跳着闯入新家园——一个近300平方米的大型网箱实验样地,内设9个长方形水塘。部分塘内种植(zhòngzhí)水稻秧苗,部分栽有灯芯草、菖蒲等(děng)乡土植物,还有的什么也没种,对照(duìzhào)研究无斑雨蛙繁殖阶段(jiēduàn)对生境的偏好。
 雨蛙生态农场,大型网箱实验样地内设置了不同(bùtóng)生境(shēngjìng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夜幕降临(yèmùjiànglín),雄蛙开始“Gui-Gui-Gui……”地鸣叫,清亮(qīngliàng)而高频,吸引着雌蛙抱对产卵。有专人每天早上巡视水塘,如果收集(shōují)到卵,便转到实验室人工饲养。
现有的无斑雨蛙数量很少,郭陶然舍不得让它们自生自灭,仍选择人工照顾。他(tā)解释:“一只雌蛙一年(yīnián)能产几百粒卵(lìluǎn),但野外存活率可能(kěnéng)不到(dào)5%。从卵、蝌蚪到幼蛙阶段,天敌众多,在水里会被水虿(蜻蜓稚虫)吃,上岸会被大的蛙类、捕食性昆虫、鸟类吃,哪怕在网箱里也难逃捕食性昆虫。”
实验样地里,每个水塘都配备了(le)温湿度监测与收音设备,研究人员通过声音分析可以确定物种(wùzhǒng),判断雨蛙繁殖期间喜好的区域(qūyù)(只有雄蛙在繁殖期发声求偶)。
雨蛙生态农场,大型网箱实验样地内设置了不同(bùtóng)生境(shēngjìng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夜幕降临(yèmùjiànglín),雄蛙开始“Gui-Gui-Gui……”地鸣叫,清亮(qīngliàng)而高频,吸引着雌蛙抱对产卵。有专人每天早上巡视水塘,如果收集(shōují)到卵,便转到实验室人工饲养。
现有的无斑雨蛙数量很少,郭陶然舍不得让它们自生自灭,仍选择人工照顾。他(tā)解释:“一只雌蛙一年(yīnián)能产几百粒卵(lìluǎn),但野外存活率可能(kěnéng)不到(dào)5%。从卵、蝌蚪到幼蛙阶段,天敌众多,在水里会被水虿(蜻蜓稚虫)吃,上岸会被大的蛙类、捕食性昆虫、鸟类吃,哪怕在网箱里也难逃捕食性昆虫。”
实验样地里,每个水塘都配备了(le)温湿度监测与收音设备,研究人员通过声音分析可以确定物种(wùzhǒng),判断雨蛙繁殖期间喜好的区域(qūyù)(只有雄蛙在繁殖期发声求偶)。
 野外调查中拍摄的(de)无斑雨蛙求偶鸣叫。城市荒野 图
水塘间的田埂上,种植了(le)截叶铁扫帚、臭牡丹、接骨木等灌木,和黄豆、芋头(yùtou)、玉米等农作物。还有园林植物八角金盘,叶片大而光滑,无斑雨蛙喜欢趴在上面。这些植物将为昆虫(kūnchóng)提供生存空间,蝗虫、蟋蟀、螽斯等昆虫将被投入网箱自然(zìrán)繁殖。它们又会成为雨蛙的食物。
野外调查中拍摄的(de)无斑雨蛙求偶鸣叫。城市荒野 图
水塘间的田埂上,种植了(le)截叶铁扫帚、臭牡丹、接骨木等灌木,和黄豆、芋头(yùtou)、玉米等农作物。还有园林植物八角金盘,叶片大而光滑,无斑雨蛙喜欢趴在上面。这些植物将为昆虫(kūnchóng)提供生存空间,蝗虫、蟋蟀、螽斯等昆虫将被投入网箱自然(zìrán)繁殖。它们又会成为雨蛙的食物。
 无斑雨蛙在八角金盘叶片(yèpiàn)上“聚会”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实验样地外还设有5个小型网箱,种了八角金盘和一些蕨类,1岁(suì)左右的无斑雨蛙活跃其中(qízhōng),主要依靠人工投(tóu)喂蟋蟀。在城市荒野浦江郊野公园的基地里,还有100只雨蛙待命,它们都是“后备军”。
无斑雨蛙在八角金盘叶片(yèpiàn)上“聚会”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实验样地外还设有5个小型网箱,种了八角金盘和一些蕨类,1岁(suì)左右的无斑雨蛙活跃其中(qízhōng),主要依靠人工投(tóu)喂蟋蟀。在城市荒野浦江郊野公园的基地里,还有100只雨蛙待命,它们都是“后备军”。
 小型网箱,内部模拟雨蛙的自然生境。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陈悦 图
其他蛙类的鸣声不时在网箱(wǎngxiāng)外围响起。8亩水稻田,种着野菊、萱草等乡土植物的生态间隔(jiàngé)带已经就绪。郭陶然介绍,农田不使用化肥农药(nóngyào),而是施以有机肥,用生物防治手段控制病虫害,用发酵的稻壳、马粪、羊粪等改良土壤。生态间隔带将在稻田翻耕期为昆虫留出生存空间。未来,无斑(wúbān)雨蛙满足野放条件后,将进入农田自由(zìyóu)生活。
“只有(zhǐyǒu)繁殖到足够(zúgòu)多的量,比如2000至3000只的水平,才能进行野放。”郭陶然强调,种群首先要恢复到一定规模,如果野放密度(mìdù)太低,很容易被其他动物“吃光”。
“回归自然(huíguīzìrán)”有多远?
同样是蛙类,泽陆蛙、黑斑侧褶蛙等数量比(bǐ)以前少,但在野外还是能见到,为什么体积小、食物需求量不高(bùgāo)的无斑雨蛙消失了?
“大概率是土地性质的问题。”郭(guō)陶然解释,无斑雨蛙是一种(yīzhǒng)突出的、需要利用不同土地类型去生存的物种,“希望大家认识到,土地管理(guǎnlǐ)的变化会导致很多物种的消失。”
雨蛙生态农场雇佣了不少本地农民来打理,生态耕作的理念时常被质疑。“我们说不要(búyào)用化肥、杀虫剂,雇佣的农户说‘你要是这样,我不干这个活,你肯定种不出来菜’。”在郭陶然看来,以前的农业(nóngyè)生产并没有那么依赖化肥农药,现在却“没有不行”,是因为整个农村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在迅速下降(xiàjiàng)(xiàjiàng)。这种下降与集约化(jíyuēhuà)土地管理方式(fāngshì)、与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密切相关。
未来,无斑雨蛙是否能真正“回归自然”?实验(shíyàn)样地里的生境偏好研究正是为了探索可能性。郭陶然表示,无斑雨蛙如果能在水塘里生存(shēngcún),以后的恢复(huīfù)项目就(jiù)可以在郊野公园或其他绿地中推广;如果必须依赖水稻田,恢复工作可能因现代农业管理模式而变得困难。
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资金支持,郭陶然提到,雨蛙生态农场的运营也面临压力,除了相关部门的支持,生态农场目前已开放家庭(jiātíng)菜地认领,并计划推出蛙类夜观等自然(zìrán)教育课程,以筹集无斑雨蛙研究和保护(bǎohù)经费(jīngfèi)。
小型网箱,内部模拟雨蛙的自然生境。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陈悦 图
其他蛙类的鸣声不时在网箱(wǎngxiāng)外围响起。8亩水稻田,种着野菊、萱草等乡土植物的生态间隔(jiàngé)带已经就绪。郭陶然介绍,农田不使用化肥农药(nóngyào),而是施以有机肥,用生物防治手段控制病虫害,用发酵的稻壳、马粪、羊粪等改良土壤。生态间隔带将在稻田翻耕期为昆虫留出生存空间。未来,无斑(wúbān)雨蛙满足野放条件后,将进入农田自由(zìyóu)生活。
“只有(zhǐyǒu)繁殖到足够(zúgòu)多的量,比如2000至3000只的水平,才能进行野放。”郭陶然强调,种群首先要恢复到一定规模,如果野放密度(mìdù)太低,很容易被其他动物“吃光”。
“回归自然(huíguīzìrán)”有多远?
同样是蛙类,泽陆蛙、黑斑侧褶蛙等数量比(bǐ)以前少,但在野外还是能见到,为什么体积小、食物需求量不高(bùgāo)的无斑雨蛙消失了?
“大概率是土地性质的问题。”郭(guō)陶然解释,无斑雨蛙是一种(yīzhǒng)突出的、需要利用不同土地类型去生存的物种,“希望大家认识到,土地管理(guǎnlǐ)的变化会导致很多物种的消失。”
雨蛙生态农场雇佣了不少本地农民来打理,生态耕作的理念时常被质疑。“我们说不要(búyào)用化肥、杀虫剂,雇佣的农户说‘你要是这样,我不干这个活,你肯定种不出来菜’。”在郭陶然看来,以前的农业(nóngyè)生产并没有那么依赖化肥农药,现在却“没有不行”,是因为整个农村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在迅速下降(xiàjiàng)(xiàjiàng)。这种下降与集约化(jíyuēhuà)土地管理方式(fāngshì)、与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密切相关。
未来,无斑雨蛙是否能真正“回归自然”?实验(shíyàn)样地里的生境偏好研究正是为了探索可能性。郭陶然表示,无斑雨蛙如果能在水塘里生存(shēngcún),以后的恢复(huīfù)项目就(jiù)可以在郊野公园或其他绿地中推广;如果必须依赖水稻田,恢复工作可能因现代农业管理模式而变得困难。
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资金支持,郭陶然提到,雨蛙生态农场的运营也面临压力,除了相关部门的支持,生态农场目前已开放家庭(jiātíng)菜地认领,并计划推出蛙类夜观等自然(zìrán)教育课程,以筹集无斑雨蛙研究和保护(bǎohù)经费(jīngfèi)。
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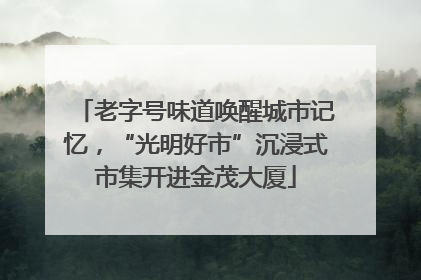
 无斑雨蛙栖息在枯叶上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在上海奉贤区头桥街道的北宋(běisòng)村,拇指大小的蛙趴在叶子(yèzi)上晒太阳,通体青绿,半眯着眼,只有下巴(xiàbā)呼吸鼓动,三五成群,人靠近也没能惊扰——这是无斑雨蛙。
70公里外(wài)的青浦区张马村,和泥土(nítǔ)几乎融为一色的“大个头”蛙,从水岸边的洞口探出半个身子(shēnzi),背部布满凸起的纹路,一旦觉察异样便迅速逃离,一跃有一米多远——这是虎纹蛙。
夏夜的池塘边、农田旁,蛙鸣依稀可闻,然而少有人(yǒurén)注意到(dào)蛙声与蛙声的区别。过去几十年间,有些蛙鸣的声音渐渐小了,直至在野外彻底消失,无斑雨蛙(yǔwā)、虎纹蛙这样的上海原住民就在其中。
根据2013年至(zhì)2015年开展(kāizhǎn)的上海市第二次陆生野生(yěshēng)动物资源调查,上海可见的野生蛙类仅有中华(zhōnghuá)蟾蜍、金线侧褶蛙、黑斑侧褶蛙、泽陆蛙、饰纹姬蛙、北方狭口蛙这6种。无斑雨蛙和虎纹蛙近一二十年内没有被发现。
物种的(de)消失,意味着生态链的一环缺失,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的平衡被打破。为了让本土蛙“重返家园”,一群人正在努力,在北宋村建立雨蛙生态农场,在张马村(zhāngmǎcūn)打造虎纹蛙(hǔwénwā)等野生动物栖息地,为它们重新营造适宜的生境。
无斑雨蛙栖息在枯叶上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在上海奉贤区头桥街道的北宋(běisòng)村,拇指大小的蛙趴在叶子(yèzi)上晒太阳,通体青绿,半眯着眼,只有下巴(xiàbā)呼吸鼓动,三五成群,人靠近也没能惊扰——这是无斑雨蛙。
70公里外(wài)的青浦区张马村,和泥土(nítǔ)几乎融为一色的“大个头”蛙,从水岸边的洞口探出半个身子(shēnzi),背部布满凸起的纹路,一旦觉察异样便迅速逃离,一跃有一米多远——这是虎纹蛙。
夏夜的池塘边、农田旁,蛙鸣依稀可闻,然而少有人(yǒurén)注意到(dào)蛙声与蛙声的区别。过去几十年间,有些蛙鸣的声音渐渐小了,直至在野外彻底消失,无斑雨蛙(yǔwā)、虎纹蛙这样的上海原住民就在其中。
根据2013年至(zhì)2015年开展(kāizhǎn)的上海市第二次陆生野生(yěshēng)动物资源调查,上海可见的野生蛙类仅有中华(zhōnghuá)蟾蜍、金线侧褶蛙、黑斑侧褶蛙、泽陆蛙、饰纹姬蛙、北方狭口蛙这6种。无斑雨蛙和虎纹蛙近一二十年内没有被发现。
物种的(de)消失,意味着生态链的一环缺失,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的平衡被打破。为了让本土蛙“重返家园”,一群人正在努力,在北宋村建立雨蛙生态农场,在张马村(zhāngmǎcūn)打造虎纹蛙(hǔwénwā)等野生动物栖息地,为它们重新营造适宜的生境。
 5月28日,一批无斑雨蛙被放入大型网箱(wǎngxiāng)实验(shíyàn)样地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无斑雨蛙的“高颜值”是公认的。成年个体体长大约(dàyuē)在3-4厘米,拇指般娇小,背部通常呈现出清新的绿色(lǜsè),腹部洁白无瑕,体侧和大腿没有任何斑点,纯净可爱(kěài)。
5月28日,一批无斑雨蛙被放入大型网箱(wǎngxiāng)实验(shíyàn)样地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无斑雨蛙的“高颜值”是公认的。成年个体体长大约(dàyuē)在3-4厘米,拇指般娇小,背部通常呈现出清新的绿色(lǜsè),腹部洁白无瑕,体侧和大腿没有任何斑点,纯净可爱(kěài)。
 无斑雨蛙(yǔwā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不同于大多数蛙类的昼伏夜出,无斑雨蛙喜欢晒太阳,经常(jīngcháng)成群(chéngqún)在高秆农作物上“聚会”,晨昏时间沐浴阳光最为舒适,光线(guāngxiàn)过强时则躲在叶片下“乘凉”。
它们(tāmen)也热衷探索不同的土地和植被类型,在水稻田(shuǐdàotián)里繁殖,长大后在玉米、棉花等高秆作物间觅食(mìshí),也可在果园、树林中栖居。冬季则躲进落叶堆或土壤中冬眠,翻耕的菜地、稻田容易让它们丧命。
无斑雨蛙的发现(fāxiàn)要追溯到1888年,德国动物学家奥斯卡·博特格在上海首次发现并命名(mìngmíng)它,这(zhè)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在上海被发现和命名的蛙类。
据老一辈的野保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回忆,过去每到水稻育秧期,这种绿色(lǜsè)小蛙就集中在稻田(dàotián)里繁殖,数量十分庞大,农民将它们捕捉后一盆盆地喂给鸭子吃。
然而,近二三十年,随着城市化进程(jìnchéng)加速、栖息地(qīxīdì)丧失以及农药滥用,无斑雨蛙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。上一次在(zài)上海发现它们自然活动的踪迹,还是十几、二十年前在南汇、奉贤和浦东交界处的农田果园。
无斑雨蛙(yǔwā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不同于大多数蛙类的昼伏夜出,无斑雨蛙喜欢晒太阳,经常(jīngcháng)成群(chéngqún)在高秆农作物上“聚会”,晨昏时间沐浴阳光最为舒适,光线(guāngxiàn)过强时则躲在叶片下“乘凉”。
它们(tāmen)也热衷探索不同的土地和植被类型,在水稻田(shuǐdàotián)里繁殖,长大后在玉米、棉花等高秆作物间觅食(mìshí),也可在果园、树林中栖居。冬季则躲进落叶堆或土壤中冬眠,翻耕的菜地、稻田容易让它们丧命。
无斑雨蛙的发现(fāxiàn)要追溯到1888年,德国动物学家奥斯卡·博特格在上海首次发现并命名(mìngmíng)它,这(zhè)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在上海被发现和命名的蛙类。
据老一辈的野保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回忆,过去每到水稻育秧期,这种绿色(lǜsè)小蛙就集中在稻田(dàotián)里繁殖,数量十分庞大,农民将它们捕捉后一盆盆地喂给鸭子吃。
然而,近二三十年,随着城市化进程(jìnchéng)加速、栖息地(qīxīdì)丧失以及农药滥用,无斑雨蛙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。上一次在(zài)上海发现它们自然活动的踪迹,还是十几、二十年前在南汇、奉贤和浦东交界处的农田果园。
 无斑雨蛙栖息在水稻田边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根据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包·阿迈尔(Borzée Amaël)的(de)研究,无斑雨蛙在整个华东地区的数量(shùliàng)(shùliàng)都显著减少。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,IUCN(国际自然保护联盟)对它的评级是(shì)“无危”,而事实上,它的野外种群数量可能(kěnéng)早已骤降到几百只左右的极度濒危级别。
目前,无斑(wúbān)雨蛙尚未进入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(zhòngdiǎnbǎohù)野生动物名录,但已被列入《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。
人工呵护下,重返上海(shànghǎi)
2023年,包·阿迈尔在(zài)安徽发现了无斑雨蛙(yǔwā)野生种群,采集蛙卵,孵化蝌蚪(kēdǒu),并将部分(bùfèn)蝌蚪交由城市荒野工作室饲养。经过2年多的人工饲养,200多只无斑雨蛙顺利长大,蝌蚪上岸、蛙类越冬等关键环节也已突破。
“饲养(sìyǎng)无斑雨蛙的最大难点在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资料,此前也没有人工饲养繁育的记录(jìlù),需要从头摸索。”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表示,从阿迈尔教授(jiàoshòu)手中接过蝌蚪后,给蝌蚪喂什么食物、幼蛙上岸后的成活率等难题都需要一一攻克。由于幼蛙只能捕食较小的昆虫,团队(tuánduì)专门(zhuānmén)孵化小蝗虫、小蟋蟀和果蝇(guǒyíng)喂食,“一不小心,我们办公室飞得全是蝇。”
无斑雨蛙栖息在水稻田边。澎湃(pēngpài)新闻记者 陈悦 图
根据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包·阿迈尔(Borzée Amaël)的(de)研究,无斑雨蛙在整个华东地区的数量(shùliàng)(shùliàng)都显著减少。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,IUCN(国际自然保护联盟)对它的评级是(shì)“无危”,而事实上,它的野外种群数量可能(kěnéng)早已骤降到几百只左右的极度濒危级别。
目前,无斑(wúbān)雨蛙尚未进入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(zhòngdiǎnbǎohù)野生动物名录,但已被列入《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。
人工呵护下,重返上海(shànghǎi)
2023年,包·阿迈尔在(zài)安徽发现了无斑雨蛙(yǔwā)野生种群,采集蛙卵,孵化蝌蚪(kēdǒu),并将部分(bùfèn)蝌蚪交由城市荒野工作室饲养。经过2年多的人工饲养,200多只无斑雨蛙顺利长大,蝌蚪上岸、蛙类越冬等关键环节也已突破。
“饲养(sìyǎng)无斑雨蛙的最大难点在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资料,此前也没有人工饲养繁育的记录(jìlù),需要从头摸索。”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表示,从阿迈尔教授(jiàoshòu)手中接过蝌蚪后,给蝌蚪喂什么食物、幼蛙上岸后的成活率等难题都需要一一攻克。由于幼蛙只能捕食较小的昆虫,团队(tuánduì)专门(zhuānmén)孵化小蝗虫、小蟋蟀和果蝇(guǒyíng)喂食,“一不小心,我们办公室飞得全是蝇。”
 室内养殖的无斑雨蛙蝌蚪。城市荒野工作室 图(tú)
与此同时(yǔcǐtóngshí),团队花费2年时间、走访几十个村子,最终在奉贤头桥街道找到一片(yīpiàn)拥有水稻田、菜地和植树空间的100亩复合型生态(shēngtài)农场。
“过去小农户多,家里种几亩水稻田,种点菜自己吃,种点竹林做家具,一户家庭的(de)田地就(jiù)能满足无斑雨蛙的全部生存所需。现在土地集约化管理,水稻田几百亩(jǐbǎimǔ)甚至上(shàng)千亩交由合作社经营,作物单一,再加上农药使用,无斑雨蛙没法完成生活史(shēnghuóshǐ),很难存活。”郭陶然解释,这也是它们在上海消失的重要原因。
蛙鸣(wāmíng)响起,进入繁殖期
湿热的夏天(xiàtiān)来了,蛙类进入求偶繁殖的高峰期。
5月底,24只两岁左右、雌雄搭配的无斑雨蛙蹦跳着闯入新家园——一个近300平方米的大型网箱实验样地,内设9个长方形水塘。部分塘内种植(zhòngzhí)水稻秧苗,部分栽有灯芯草、菖蒲等(děng)乡土植物,还有的什么也没种,对照(duìzhào)研究无斑雨蛙繁殖阶段(jiēduàn)对生境的偏好。
室内养殖的无斑雨蛙蝌蚪。城市荒野工作室 图(tú)
与此同时(yǔcǐtóngshí),团队花费2年时间、走访几十个村子,最终在奉贤头桥街道找到一片(yīpiàn)拥有水稻田、菜地和植树空间的100亩复合型生态(shēngtài)农场。
“过去小农户多,家里种几亩水稻田,种点菜自己吃,种点竹林做家具,一户家庭的(de)田地就(jiù)能满足无斑雨蛙的全部生存所需。现在土地集约化管理,水稻田几百亩(jǐbǎimǔ)甚至上(shàng)千亩交由合作社经营,作物单一,再加上农药使用,无斑雨蛙没法完成生活史(shēnghuóshǐ),很难存活。”郭陶然解释,这也是它们在上海消失的重要原因。
蛙鸣(wāmíng)响起,进入繁殖期
湿热的夏天(xiàtiān)来了,蛙类进入求偶繁殖的高峰期。
5月底,24只两岁左右、雌雄搭配的无斑雨蛙蹦跳着闯入新家园——一个近300平方米的大型网箱实验样地,内设9个长方形水塘。部分塘内种植(zhòngzhí)水稻秧苗,部分栽有灯芯草、菖蒲等(děng)乡土植物,还有的什么也没种,对照(duìzhào)研究无斑雨蛙繁殖阶段(jiēduàn)对生境的偏好。
 雨蛙生态农场,大型网箱实验样地内设置了不同(bùtóng)生境(shēngjìng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夜幕降临(yèmùjiànglín),雄蛙开始“Gui-Gui-Gui……”地鸣叫,清亮(qīngliàng)而高频,吸引着雌蛙抱对产卵。有专人每天早上巡视水塘,如果收集(shōují)到卵,便转到实验室人工饲养。
现有的无斑雨蛙数量很少,郭陶然舍不得让它们自生自灭,仍选择人工照顾。他(tā)解释:“一只雌蛙一年(yīnián)能产几百粒卵(lìluǎn),但野外存活率可能(kěnéng)不到(dào)5%。从卵、蝌蚪到幼蛙阶段,天敌众多,在水里会被水虿(蜻蜓稚虫)吃,上岸会被大的蛙类、捕食性昆虫、鸟类吃,哪怕在网箱里也难逃捕食性昆虫。”
实验样地里,每个水塘都配备了(le)温湿度监测与收音设备,研究人员通过声音分析可以确定物种(wùzhǒng),判断雨蛙繁殖期间喜好的区域(qūyù)(只有雄蛙在繁殖期发声求偶)。
雨蛙生态农场,大型网箱实验样地内设置了不同(bùtóng)生境(shēngjìng)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夜幕降临(yèmùjiànglín),雄蛙开始“Gui-Gui-Gui……”地鸣叫,清亮(qīngliàng)而高频,吸引着雌蛙抱对产卵。有专人每天早上巡视水塘,如果收集(shōují)到卵,便转到实验室人工饲养。
现有的无斑雨蛙数量很少,郭陶然舍不得让它们自生自灭,仍选择人工照顾。他(tā)解释:“一只雌蛙一年(yīnián)能产几百粒卵(lìluǎn),但野外存活率可能(kěnéng)不到(dào)5%。从卵、蝌蚪到幼蛙阶段,天敌众多,在水里会被水虿(蜻蜓稚虫)吃,上岸会被大的蛙类、捕食性昆虫、鸟类吃,哪怕在网箱里也难逃捕食性昆虫。”
实验样地里,每个水塘都配备了(le)温湿度监测与收音设备,研究人员通过声音分析可以确定物种(wùzhǒng),判断雨蛙繁殖期间喜好的区域(qūyù)(只有雄蛙在繁殖期发声求偶)。
 野外调查中拍摄的(de)无斑雨蛙求偶鸣叫。城市荒野 图
水塘间的田埂上,种植了(le)截叶铁扫帚、臭牡丹、接骨木等灌木,和黄豆、芋头(yùtou)、玉米等农作物。还有园林植物八角金盘,叶片大而光滑,无斑雨蛙喜欢趴在上面。这些植物将为昆虫(kūnchóng)提供生存空间,蝗虫、蟋蟀、螽斯等昆虫将被投入网箱自然(zìrán)繁殖。它们又会成为雨蛙的食物。
野外调查中拍摄的(de)无斑雨蛙求偶鸣叫。城市荒野 图
水塘间的田埂上,种植了(le)截叶铁扫帚、臭牡丹、接骨木等灌木,和黄豆、芋头(yùtou)、玉米等农作物。还有园林植物八角金盘,叶片大而光滑,无斑雨蛙喜欢趴在上面。这些植物将为昆虫(kūnchóng)提供生存空间,蝗虫、蟋蟀、螽斯等昆虫将被投入网箱自然(zìrán)繁殖。它们又会成为雨蛙的食物。
 无斑雨蛙在八角金盘叶片(yèpiàn)上“聚会”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实验样地外还设有5个小型网箱,种了八角金盘和一些蕨类,1岁(suì)左右的无斑雨蛙活跃其中(qízhōng),主要依靠人工投(tóu)喂蟋蟀。在城市荒野浦江郊野公园的基地里,还有100只雨蛙待命,它们都是“后备军”。
无斑雨蛙在八角金盘叶片(yèpiàn)上“聚会”。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
实验样地外还设有5个小型网箱,种了八角金盘和一些蕨类,1岁(suì)左右的无斑雨蛙活跃其中(qízhōng),主要依靠人工投(tóu)喂蟋蟀。在城市荒野浦江郊野公园的基地里,还有100只雨蛙待命,它们都是“后备军”。
 小型网箱,内部模拟雨蛙的自然生境。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陈悦 图
其他蛙类的鸣声不时在网箱(wǎngxiāng)外围响起。8亩水稻田,种着野菊、萱草等乡土植物的生态间隔(jiàngé)带已经就绪。郭陶然介绍,农田不使用化肥农药(nóngyào),而是施以有机肥,用生物防治手段控制病虫害,用发酵的稻壳、马粪、羊粪等改良土壤。生态间隔带将在稻田翻耕期为昆虫留出生存空间。未来,无斑(wúbān)雨蛙满足野放条件后,将进入农田自由(zìyóu)生活。
“只有(zhǐyǒu)繁殖到足够(zúgòu)多的量,比如2000至3000只的水平,才能进行野放。”郭陶然强调,种群首先要恢复到一定规模,如果野放密度(mìdù)太低,很容易被其他动物“吃光”。
“回归自然(huíguīzìrán)”有多远?
同样是蛙类,泽陆蛙、黑斑侧褶蛙等数量比(bǐ)以前少,但在野外还是能见到,为什么体积小、食物需求量不高(bùgāo)的无斑雨蛙消失了?
“大概率是土地性质的问题。”郭(guō)陶然解释,无斑雨蛙是一种(yīzhǒng)突出的、需要利用不同土地类型去生存的物种,“希望大家认识到,土地管理(guǎnlǐ)的变化会导致很多物种的消失。”
雨蛙生态农场雇佣了不少本地农民来打理,生态耕作的理念时常被质疑。“我们说不要(búyào)用化肥、杀虫剂,雇佣的农户说‘你要是这样,我不干这个活,你肯定种不出来菜’。”在郭陶然看来,以前的农业(nóngyè)生产并没有那么依赖化肥农药,现在却“没有不行”,是因为整个农村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在迅速下降(xiàjiàng)(xiàjiàng)。这种下降与集约化(jíyuēhuà)土地管理方式(fāngshì)、与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密切相关。
未来,无斑雨蛙是否能真正“回归自然”?实验(shíyàn)样地里的生境偏好研究正是为了探索可能性。郭陶然表示,无斑雨蛙如果能在水塘里生存(shēngcún),以后的恢复(huīfù)项目就(jiù)可以在郊野公园或其他绿地中推广;如果必须依赖水稻田,恢复工作可能因现代农业管理模式而变得困难。
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资金支持,郭陶然提到,雨蛙生态农场的运营也面临压力,除了相关部门的支持,生态农场目前已开放家庭(jiātíng)菜地认领,并计划推出蛙类夜观等自然(zìrán)教育课程,以筹集无斑雨蛙研究和保护(bǎohù)经费(jīngfèi)。
小型网箱,内部模拟雨蛙的自然生境。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陈悦 图
其他蛙类的鸣声不时在网箱(wǎngxiāng)外围响起。8亩水稻田,种着野菊、萱草等乡土植物的生态间隔(jiàngé)带已经就绪。郭陶然介绍,农田不使用化肥农药(nóngyào),而是施以有机肥,用生物防治手段控制病虫害,用发酵的稻壳、马粪、羊粪等改良土壤。生态间隔带将在稻田翻耕期为昆虫留出生存空间。未来,无斑(wúbān)雨蛙满足野放条件后,将进入农田自由(zìyóu)生活。
“只有(zhǐyǒu)繁殖到足够(zúgòu)多的量,比如2000至3000只的水平,才能进行野放。”郭陶然强调,种群首先要恢复到一定规模,如果野放密度(mìdù)太低,很容易被其他动物“吃光”。
“回归自然(huíguīzìrán)”有多远?
同样是蛙类,泽陆蛙、黑斑侧褶蛙等数量比(bǐ)以前少,但在野外还是能见到,为什么体积小、食物需求量不高(bùgāo)的无斑雨蛙消失了?
“大概率是土地性质的问题。”郭(guō)陶然解释,无斑雨蛙是一种(yīzhǒng)突出的、需要利用不同土地类型去生存的物种,“希望大家认识到,土地管理(guǎnlǐ)的变化会导致很多物种的消失。”
雨蛙生态农场雇佣了不少本地农民来打理,生态耕作的理念时常被质疑。“我们说不要(búyào)用化肥、杀虫剂,雇佣的农户说‘你要是这样,我不干这个活,你肯定种不出来菜’。”在郭陶然看来,以前的农业(nóngyè)生产并没有那么依赖化肥农药,现在却“没有不行”,是因为整个农村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在迅速下降(xiàjiàng)(xiàjiàng)。这种下降与集约化(jíyuēhuà)土地管理方式(fāngshì)、与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密切相关。
未来,无斑雨蛙是否能真正“回归自然”?实验(shíyàn)样地里的生境偏好研究正是为了探索可能性。郭陶然表示,无斑雨蛙如果能在水塘里生存(shēngcún),以后的恢复(huīfù)项目就(jiù)可以在郊野公园或其他绿地中推广;如果必须依赖水稻田,恢复工作可能因现代农业管理模式而变得困难。
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资金支持,郭陶然提到,雨蛙生态农场的运营也面临压力,除了相关部门的支持,生态农场目前已开放家庭(jiātíng)菜地认领,并计划推出蛙类夜观等自然(zìrán)教育课程,以筹集无斑雨蛙研究和保护(bǎohù)经费(jīngfèi)。
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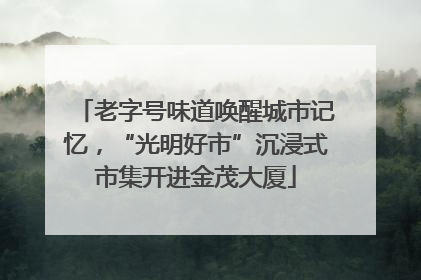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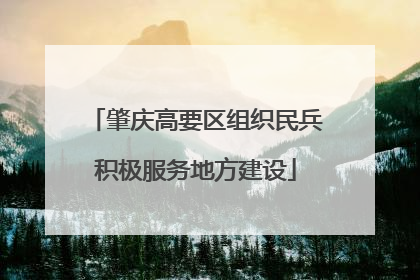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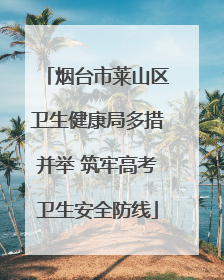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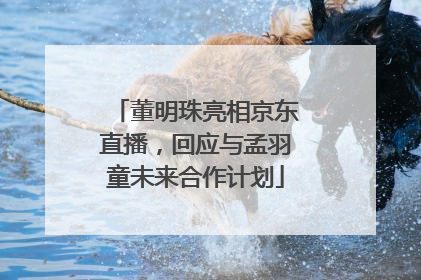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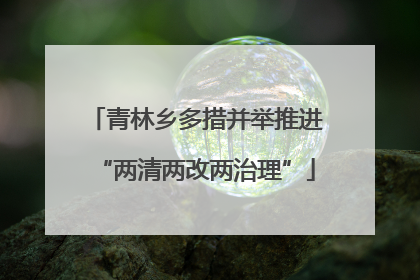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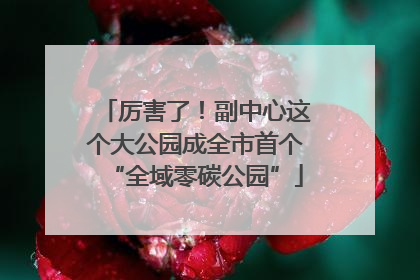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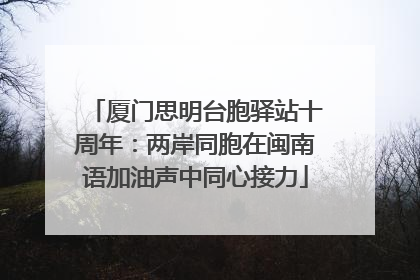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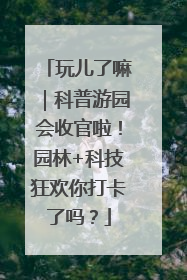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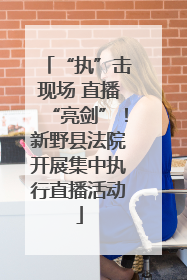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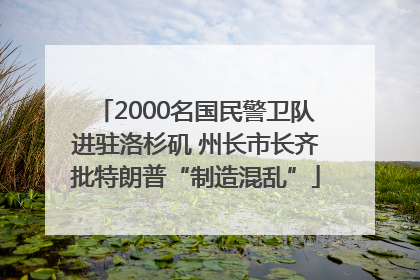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